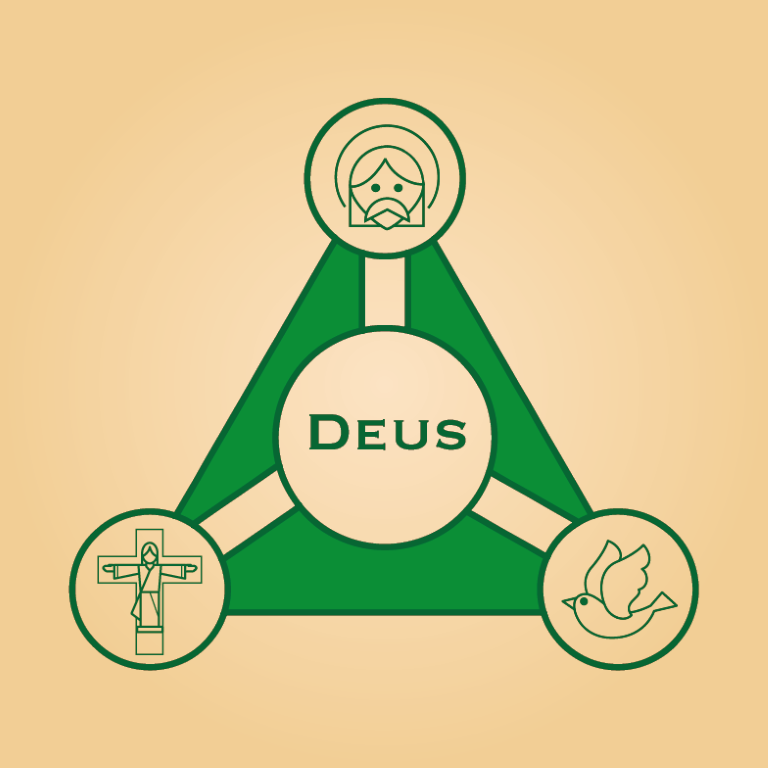專訪教區歷史檔案及文物處辦公室主任(2)
葉家祺:檔案和文物工作,每次都是全新的相遇
文化遺產和文物的保護有趣的地方是?
我經常和朋友們分享說,在檔案和文物工作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一次都是全新的相遇。每件單一的檔案與文物都是獨立的個體。試想像:兩本一模一樣的古書,一本內有教宗的簽名,其保留方式及修復需求亦顯而易見。
我們時常聽到的「最少干預原則」,也是一種保護。接續上述例子,若以現代的手法修復一本古書,最終我們會看到一本十分精緻的圖書。但是這樣反而破壞了該古書原本的呈現方式。所以,我們修復這本書的定位應是以最少的干預為方向,將這文物最真實和具有歷史價值的一面呈現出來。
我認為,有時候看到文物的損傷為我們後人也是上了珍貴的一課。
關於文物修復呢?
基本上,我們每天都需要去審視和研究哪一些檔案或文物需要修復工作的介入,當然我們要先為文物評級分類,判斷優先次序,再開始研究整個修復的程序和過程。我們更多的時候是做預防性的工作,默默守護我們的文獻和遺產。
修復工作方面,每年我們約處理十多宗個案,每個個案都涉及一件或幾件的文物。比如最近我們正在處理九澳聖母村內已損毀的聖像,當中有一件我們比較重視的,是一尊位於七苦聖母堂前的聖母像,是夏剛志先生捐贈給聖堂的,那尊聖母像肯定是值得保留和維護。
通常修復一件文物涉及的費用如何?
要視乎其受損程度、製作年代所使用的技法、所需的進口物料、修復師的資歷和技術等,所以沒有特定的標準。比如去年我們立案修復了兩卷在聖若瑟修院使用的教材。它是一批約50多卷的醋酸菲林,由於受損情況(受潮、受熱等情況)嚴重,而且醋酸菲林有別於一般的菲林,所以需要請擁有相關知識的修復師處理。要完全修復所有的醋酸菲林價值不菲,但菲林所承載的歷史資料很珍貴,所以其價值也不能與金錢完全劃上等號的。我們也在等待恩人能資助相關的項目,共同在文物保育工作上作出貢獻。

到目前為止,您在修復工作中最深刻的是哪一宗個案呢?
應該是教區主教油畫系列:位於主教府內歷代澳門教區主教的油畫,原本我們分了三期去處理修復的工作的。由於疫情關係,現時我們只做了一期,共七幅主教油畫,到現在也未能繼續去推進這個工作。在這次修復過程中,我們發現所有主教的油畫猶如一個微型的藝術史。當中有不同世紀風格的畫風與手法,亦有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畫家,不同的物料與內容,畫師對主教的理解,以及畫師如何呈現該主教最特別的意義,所以每一幅畫都會看到與別不同的資訊,為我而言十分深刻。
此外,每幅畫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例如:畫布斷裂、顏料層剝落、畫板爆裂,或有些受到高溫、水浸、發霉等影響。
得悉您們最近也修復了聖屍聖像……
是2021年完成的。修復團隊花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去修復聖屍聖像。教會中一部分的文物,包括聖屍聖像、聖爵等,其實是仍然使用中。而使用中的聖像,必然會受損的,比如受到天氣溫濕度的影響,特別是出遊時對聖像的損害程度更甚。因為移動時或信友觸摸時,會令聖像結構因碰撞而受損、接觸位置脫色等。這些情況就需要請專業人士修復相關損毀物品。而聖屍聖像的枕頭、祭衣、祭披等,便需要找專門製作祭衣的裁縫。
教會不是博物館,她是旅途中的教會,要不斷地活出信仰。所以這些文物的見證,需要每天重新呈現出來,不斷更新它們的意義,才能讓我們繼續透過這些有形的遺產在新時代中延續這份恩寵。
為您而言,最具挑戰、最困難的是甚麼呢?
我們永遠都有進步的空間,不能輕易用同一套法則應用到每一件事情上。每次處理新的個案,都會衍生出不同的情況及處理方法,要不斷迎接新挑戰。而且,在修復的過程中,著眼的不應只是用什麼技術去拯救文物,而是反思這些文物承載了什麼價值,我們又能如何把這些價值延續下去,這才是至關重要的事。
目前我和團隊們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以現代的思維,技術和修復方式,為眾多的檔案和文物進行編目和保存工作,延續先賢先哲們的工作。我唯一能夠非常肯定地說,即使我花畢生的精神和時間也是做不完這事的。但是能做多少便做多少,其他不堪當的部分就托付給天主吧。


 Follow
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