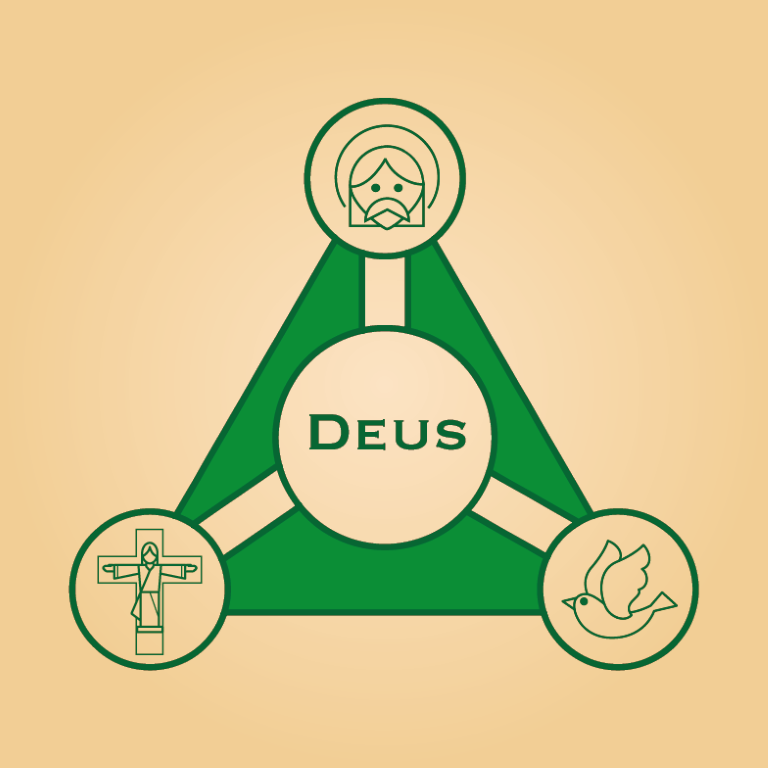文:Marco Carvalho
譯:寓風
聖言會傳教士範聖言神父(Franz Gassner)接替剛上任聖若瑟大學校長的麥侍文執事,成為該校宗教研究學院院長。出生於奧地利的範神父接受《號角報》訪問,指出與中國以及整個亞洲文化建立理解的橋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重要,而且是勢在必行的。
這是你職業生涯的一個新階段、新挑戰。你對這次任命有甚麼期待?你將要應對的主要問題是甚麼?
主要問題?如何好好服務學生和教師,如何讓校園成為一個切切實實的跨文化團體。在這裡,宗教研究學院有來自不同國家和文化的學生和教職員。我們一起學習、一起工作、力求更了解彼此、互相幫助、當然,也準備為東南亞及周邊教會和社會的福傳作準備。的確,對於我們的學生而言,學術研究是一項挑戰。他們必須學習困難的語言,如: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用英語撰寫和答辯研究論文。對一些學生而言,學習這些語言並不容易,但是,這尤其為修讀神學是一個重要的部分。為他們將來的服務做好充分的準備,是非常重要的,以便他們可以研讀「神聖教義」(Sacra Doctrina),或者在神學和現代社會上涉及的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
正如你提及,我們談論的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這會怎樣影響對學生的教學方式?學院如何應對這種文化差異?
作為員工、學生以及整個的學習團體,學會善於傾聽和溝通,是至關重要的。學生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問題和經驗。當他們撰寫論文時,他們還可以反思自己的祖國和文化所面臨的挑戰。同樣,我們的教授也非常國際化,對處理這些問題很有幫助。我們也舉行慶祝活動,歡迎學生出席並分享他們的傳統——他們祖國的舞蹈、傳統服裝、傳統菜式和美食。這些活動真是美妙的,並幫助我們在多樣性中和精神上建立某種程度的合一。目前,我們有64位神學學生和四位宗教研究博士生。神學學生中,有13位來自澳門教區修院的修生和「救主之母」(Redemptoris Mater)公學,有25位準備鐸職的修士(24位道明會士和1位聖言會士)、22位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望會生,和四位平信徒學生。除了這些學生以外,我們還有來自聖若瑟大學其他學系的碩士生——哲學碩士生、歷史學碩士生或歷史與遺產研究碩士生——均使用我們的圖書館資源。我們的圖書館將在未來幾年增添館藏。李斌生主教正協助和幫助我們,將我們學科領域中不同圖書館的資源整合在一起,當中包括哲學、宗教學、神學、教會歷史或中國及亞洲歷史。澳門有很多的資源,但必須先將它們整合在一起,讓研究人員(如碩士生、博士生或其他國際研究人員)可以使用。這項工作正在進行中,也是我們新任校長麥侍文執事與澳門教區和澳門其他機構合作的主要重點之一。
你剛提到那個圖書館的位置,將會在學院再作整合嗎?
不會,相反,它將保留在地下樓層,然後進行翻新和技術更新,並與宗教研究學院的圖書館合併。目前,聖若瑟舊修院的現有圖書館與我們這裡的圖書館將合併在一起,以建立一個更大的圖書館。我們的學生和研究人員都可以使用該圖書館。這確實是非常重要。
直到20世紀中期,聖若瑟修院是一所非常重要的機構,現在我們正在見證一個「重生」。澳門會再次成為東亞區傳福音的中心嗎?如此的「重生」能否幫助澳門恢復以前的宗教地位?
我認同的。我認為這已在進行中,以恢復或繼續這傳統。幾個世紀以來,澳門培育教友和修道人,以致他們可以幫助教會和促進亞洲區的福音傳播工作。這種培育不僅是為澳門,也為許多東南亞的其他地區。這裡有着悠久的傳統,我認為這傳統正在復興,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必須非常感激這個歷史的機遇。幸運的是,我們在澳門擁有非常具價值的東西,就是宗教自由和研究自由。這是個極具價值的一面。在我看來,對於澳門、大中華地區,甚至整個亞洲而言,都有一個可以修讀和進行哲學、神學、宗教研究、歷史研究的地方。這容許各地——如:中國和西方傳統之間——建立持久的理解橋樑;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我們很幸運,目前有為數不少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的學生,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國際系教授和客席教授。我們很有福,這些學生和教授可以來到這裡;我們不能認為他們能來聖大,是理所當然的事。另一方面,我們也有機會與歷史聯繫起來,特別是在澳門這裡。利瑪竇在澳門學習中文和文化,首位韓國聖人在這裡修讀神學,還有其他更多的例子。是的,澳門可以再次成為一個如此重要的地方。
你強調了一個事實:在澳門,我們仍享有宗教自由。然而,在邊境的另一端,情況並不一樣。宗教研究學院是否開放接待來自中國大陸的修生?你認為有可能在未來幾年發生嗎?
我希望這窗口有天能確切地打開,我希望這將會成為可能的。我認為進行更直接的交流是非常重要,以致我們才能一起學習,並在更深的層次上更理解彼此。當然,這也符合整個圖畫:我們在這裡互相服務、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尤其是為中國教會服務。實際上,在台灣,這已經成為可能的了。修生可以留在台灣三年,我們希望這裡也有這個可能性。我希望能夠發展這種交流,並且,將來在聖若瑟大學,我們也可以成為來自中國修生學習和交流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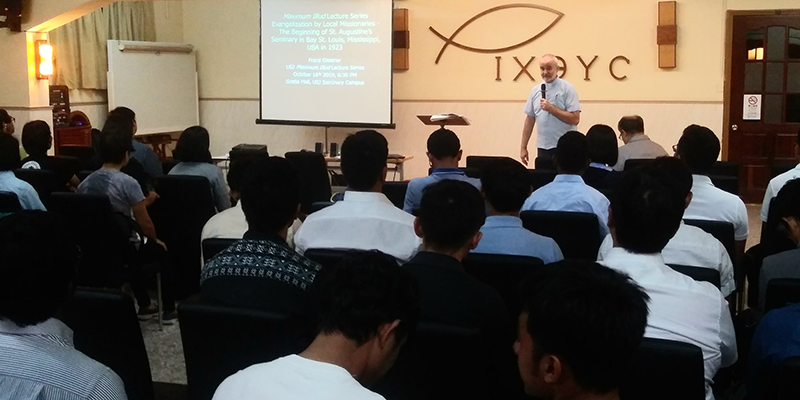
正如你說,神學院不只是為修生或修道人,也為平信徒。現時已有一些平信徒,為更了解信仰,甚至為更了解自己,而修讀神學。平信徒開始對你所教的東西有興趣,這是一個重要的部分嗎?
以有系統的方式修讀神學和哲學,對教會和社會都非常重要。當然,現時我們必須先為目前的38位聖秩候選人服務。我們也很有福,有數位玫瑰道明傳教女修會的望會生與我們一起學習,她們仍然是平信徒,但若她們願意,日後也能成為修女。我們很有福、也很高興有四位平信徒學生,一起修讀哲學和神學。他們準備以不同的方式為教會和社會服務:在教區、在教育、在社區建設、在法律、在傳媒、在學術研究,甚至可能像其他國家一樣為政府服務。而且,歷史學家和研究人員某程度上必須修讀神學科目或拉丁文,特別是那些修讀教會史的。教會和社會都需要更多的人、更好的準備,以便在不同文化和傳統之間建立理解的橋樑。實際上,這是至關重要。當然,神職聖召對教會非常重要,但教會也需要修讀哲學和神學的平信徒,以協助教會在不同領域上的發展和服務。
宗教研究學院的目標是甚麼?是要準備神父和合資格的人士,好能服務澳門?還是打算為亞洲地區服務?你曾提及大多數在澳門修讀的修生來自越南、東帝汶、緬甸等地。他們晉鐸後會回到自己的地方嗎?
在宗教學院,在修讀聖職的學生中,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學生。我們有本地教區的人;有七位學生來自本地教區。如你所知,他們當然會服務本地教區,因為澳門需要本地的神父。然後,去年在澳門成立的第二所神學院——新慕道者團體的「救主之母」公學——我估計這些學生完成學業後,將在不同的國家傳教。然後,我們有為聖秩作準備的道明會士,他們佔的人數最多。道明會的校友將擔任傳教士,他們會去東帝汶、越南、緬甸,及至台灣。其中一位去年完成學業的學生,最後被派往西班牙,他在那裡學習西班牙文並繼續進修。對於你的問題的答案,是我們同時為澳門及其他地區提供服務:我們是「天主教徒」,這意味着「全面性」或「普世性」的。這也完全符合澳門教會培育的悠久傳統。
在過去幾年,主要是在歐洲和西方國家,一直討論缺乏聖召的議題。這是否確實是一個問題呢?
當然,教會需要聖召,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加強家庭牧民。我們需要有聖德的家庭,我們需要有聖德的人;如此,聖召才可以從中滋長和發展,因此我們需要加強家庭牧民。教會當然需要聖召,但是,聖召不只局限於司鐸聖召。一個平信徒對教區、教會和社會也有着一個非常重要的召叫和使命。執事聖召非常重要。在社會活動或教育領域上,在澳門服務的修女擔當着偉大的福傳工作。教會需要不同的召叫,我們必須不斷祈求天主召叫工人進入祂的葡萄園。當然,我們必須為更多的聖召祈禱:司鐸聖召、執事聖召、修道聖召,以及充滿聖德的家庭的召叫等。對我而言,這是非常清楚。
以個人來說,作為宗教研究學院院長的使命,你預期會有甚麼好的結果?你有沒有一些個人的目標渴望要達到呢?
神學實際上是大學的根源。現代大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教授文科和神學的主教座堂學校(Domschule)。哲學是有需要的,在那裡哲學得以強化和發展。從這些主教座堂學校(如巴黎聖母院)誕生了首批現代大學(巴黎大學)。從哲學開始,逐步發展出科學。正如校長麥侍文執事所強調的,我們不應忽視這根源,即:神學是科學之后,哲學是忠僕。我認為,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去恢復這原始的傳統,以便更好地服務整所大學和整個社會。神學院探討或研究許多非常重要的問題,當中涉及生命的最終意義、有關天主[的知識]、神修和宗教傳統、道德上的挑戰等。神學提倡一種有承擔的、有系統性的和有責任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基本的照題。這是學院為整個大學、整個教會和整個社會,所提供非常重要的服務。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會有缺失或偏離,最終導致我們陷入危機。

 Follow
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