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rco Carvalho
譯:何紹玲
要談澳門,便要談到天主教在澳門的悠久歷史, 近五百多年來,一直離不開與葡萄牙在東亞洲的密切關係。這城市是遠東地區最源遠流長的教區,但在葡萄牙統治的最初幾年,這裏的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尤其被迫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的影響力是超乎大家所預料的。東京外國語大學研究學者Lúcio de Sousa認為,這種影響伸展到日本。在那裡,商界差不多都被新基督教徒所操控,當擴展到日本,更成為日本耶穌會的主要盟友。這位葡萄牙籍的學者Lúcio de Sousa在接受《號角報》的訪問時,重温天主聖名之城(City of the Holy Name of God)早年的點滴。
去年11月教宗方濟各出訪日本期間,長崎也是他到訪過的地方之一,它不僅是日本天主教歷史重要的城市,更在東西方之間的關係上環環相扣、息息相關,是一個標誌性城市。但若沒有澳門,這種關係根本不可能拉得上,從此長崎便一直與澳門有着密切的聯繫……
我覺得這不單單只是一個重要的聯繫,而是獨有的聯繫,是最重要的一環。但自1640年,這聯繫曾被中斷,直至19世紀——日本對外開放——聯繫才再次恢復。當第一批外交代表在長崎成立時,澳門再次列在前線。就以蘇沙(Souza)家族為例,這氏族在澳門和新加坡都很顯赫,現時至少仍有一位後裔是以日本為家的。我曾和他傾談過,他把家中一些文件給我看,有些更是他與家人初踏足日本時的文件。稍後,我更找到他們在神戶的歐洲外交圈中,是如何地舉足輕重,而澳門的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這個聯繫實在是個不容爭辯的事實。沒有澳門,便沒有長崎,便沒有葡國人能在日本踏足;就是通過澳門,一個教學和教育的平台隨之成立,成為培育歐洲和日本傳教士的平台。每年也會有數批日本學生前往澳門,在耶穌會創立的聖保祿學院攻讀,目的是希望學成返國後,能令日本人民皈依天主教。
不少傳教士從澳門來到長崎,但他們並不是唯一在這方面竭力的人;還有那些皈依的猶太人,都來到遠東碰碰運氣。這就說明你進行的一些調查所證實的那樣,這是一種比人們推測更為普遍的現象……
同意、同意!澳門在當時葡萄牙王國眼中,往往處於不受重視的地位。那時候要前往澳門並不容易;如果對新基督徒或皈依者已不容易,為司法機構也不會容易。來到亞洲這地區、定居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多是逃犯。我們要牢記,大部份登上印度貿易船隻的船員,實際上都是罪犯。當他們一抵達果亞(Goa),便會試圖擺脫葡萄牙司法權力可達至的範圍,去到一些可以讓他們安全地生活的地方:例如初期的馬六甲或後期的澳門。在澳門,葡萄牙的存在本身是一個有條件的存在。換句話說,[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但此殖民地並非完全屬於葡國,因為我們談的是一個共同的領土,而在這片領土上,中國可以行駛一定的權力。[因此,葡國的權力]是一個具協商而又脆弱的存在。自此,尤其自1560年果亞成立宗教裁判所以後,澳門便成為一個進教福地。當時,因一場蔓延到馬六甲的迫害風波,令果亞和科欽(Cochin)的第一批教友團體瓦解了。澳門結果在1557年正式成為殖民地,有報導稱在1555年已有葡萄牙人在該地區生活。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費爾南.門德斯.平托( Fernão Mendes Pinto)在他的書信中也有提及。於是,澳門便成為這些逃犯自由出入的地方了,他們包括罪犯和被降級的人,更有想逃離印度的新基督徒。但我們也不應忽畧在15和16世紀——甚至更早的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葡萄牙的貿易基本上是由猶太血統的大家族所控制的。當國王曼紐一世決定猶太人不能再留在葡萄牙時,他虛構了一種集體皈依的念頭,他為何有此一着?在經濟而言,猶太人在葡萄牙社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歐洲其他任何法院中都不會找到一幅畫像:畫中人物是葡萄牙王室與主教,但也有一位非基督徒的宗教人物,他是位猶太人,一位辣比(rabbi老師),旁邊還有打開了的梅瑟五書。這已表明猶太人在葡萄牙社會中的重要性以及他們與王室的聯繫是如何緊密。
第一位來到歐洲的中國婦女,都是全賴基督徒的幫忙。我們說的是誰呢?
我對宏觀的歷史活動很感興趣,但別忘記歷史都是由人創造的。除了研究偉大的歷史活動,我更喜歡從歷史中尋找那些和歐洲或歐陸文化有接觸的人。其中有一個來自廣東省的女孩,於大概1560年,本想從南中國前往日本,卻在旅途的船上領了洗;稍後,我們也會在另兩艘主要運送婦女的船隻上再次找到她——這些婦女注定成為葡萄牙士兵和商人的性奴——最初她被送往馬六甲、隨之送到印度,並在科欽被販賣給一名叫Lalanda de Menezes的葡籍牙或印葡籍婦人。之後她再被轉賣到果亞一個名叫Milão的新基督徒富裕家庭,隨着這家庭去了里斯本,為這家庭當廚子。最後,她雖被這家庭釋放了,但還留下來為他們工作,而因葡萄牙宗教裁判(1536年)的關係,這家庭便成了迫害的目標。有見及此,她利用自己奴隸的身份,發揮了她基本的作用,順利幫助這家庭逃到葡萄牙宗教裁判所沒權力的歐洲國家,最後在德國漢堡終老。至於這家庭亦繼續往前走,最後定居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我剛巧認識那家庭的後裔,我們經常通話。

你提到一個不被正視的重要問題,談到奴隸制,我們多聯想到大西洋的奴隸販賣,可是葡萄牙和歐洲的帝國不也一樣在亞洲提倡奴隸制嗎?
對!奴隸制並不是葡萄牙帝國產生的現象,自有人類以來,各部族也會試圖征服對方,這機制一直沿用了數千年,已被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等地徹底利用……其實是被所有歐洲大國所利用,沒有例外的,最近期的國家大概是比利時吧,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King Leopold )可算是最殘酷的君王,也可能是從19世紀奴隸制中得益最大的人。說到葡國的奴隸制,大家必會聯想到這是一項非常多元化的事業。葡萄牙人在亞洲行使的奴隸制,因不受皇室監控,與大西洋沿用的很不同,它之發生是出於自發,故也很自然地沿用至19世紀,起碼在澳門……在那裏,我們找到苦力。在法律上,苦力不能被視為奴隸,但實際上,以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與奴隸是沒分別的。更有人指出這制度是來自美國,都是因為非洲人和棉花田的關係。亦有指是巴西版定型化,聲稱奴隸在大型咖啡種植場都是一樣為葡萄牙主人勞役。當然,這種奴役是實在的,但在亞洲不同的國家,他們會用買來的奴隸去配合不同的工種。大規模的種植園是不會用奴隸的,他們主要是當家傭,澳門便可找到不少,大多數的家庭都有奴隸,他們來自四面八方:有韓國、印度、孟加拉、日本、馬來西亞及帝汶,甚至整個東南亞。這些婦女的來歷差别很大。但隨着歷史演變,很多事情也改變了質,從初期主要是中國奴隸,至第二個時期變成絕大多數來自日本和韓國,從中國來的仍有很多,更有不少來自東南亞。但奴隸制這議題涉及不同的界限,不僅是表面的,更是廣泛的。
在日本那些奴隸是從那兒來的?耶穌會士有奴隸嗎?
當然,耶穌會士會試圖從他們的記錄中抹去這些資料,但只要翻閱耶穌會士在日本的規章,你便會看到他們有一章節,提及應該如何對待奴隸、獲得奴隸的途徑和如何教育他們等等。這些書明確地揭示了他們試圖隱藏曾參與奴隸制的實情。關於這點,我亦曾撰文。此外,當我們開始研究那些主要是中國和日本血統的奴隸,而最終卻到了美國的檔案時,發覺他們之能被轉賣到海外,護照都是由耶穌會士發出,是他們一手創造這種護照的;是他們評估那些奴隸、是他們將這些奴隸合法化為永久的奴隸,並允許奴隸可以在任何港口被販賣,而這些一般都不是奴隸原本的條件。
我的最後一個問題——現仍有待調查——是有關歐/日之間建立的關係問題,是否在日本的歷史或日本與外界交往的歷史中已經清楚交代了?
那便要視乎情況……這個問題不容易答。每個國家都會有自己不同的固定形式,日本也不例外。要知道,有兩個方法:可以遊客身份訪問一個國家;或到那個國家定居。去深入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我們便認識到,這種文化有幾個特徵,未必符合所有定型觀念的。但只要還有歷史,就可以運用不同的方法;只要還有想像力、繼續分析和研究的決心,我們肯定在各種文化上發現新的事物。我認為這是一個可拓展的領域;只要日本還存在,這個可拓展領域便會長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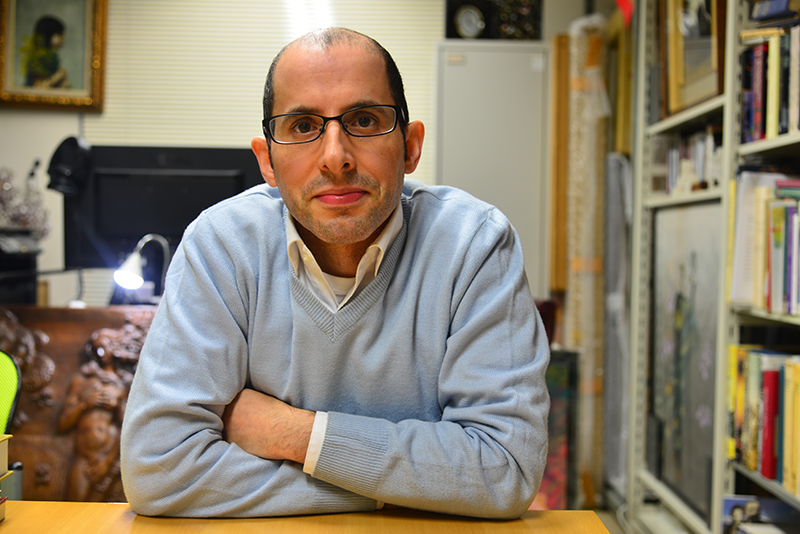
 Follow
Fol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