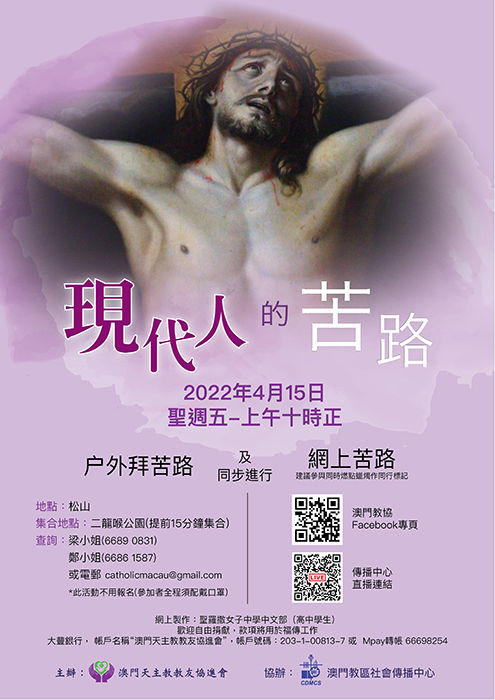文:FAUSTO GOMEZ OP
譯:何紹玲
在這專題的第二部份,我們會在活體器官捐獻和接受器官捐獻者這些議題上作點思考。
- 器官捐獻者:活體捐贈
在活體器官捐獻這議題上,主要的兩個倫理問題都與身體的完整性和捐獻作出允許。有關活體器官捐獻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可以是自己的活體器官(例如腎臟)的捐獻者嗎?
作為人類, 我是一個個體,也是一個人,更是人類家庭成員之一;作為一個自律的個體,我是不可分割和獨特的:我便是肉體加靈魂,或精神體進入血肉。我是個別 人士,所以我不僅是自律的個體,更是(他律)關係性存在者。我是人類家族的一員,我以愛和團結的精神與他人團結在一起。
作為一個基督信徒,生命是屬於天主的,我只是我自己生命的管理人,也是聖教會內耶穌的一名信徒,是信、望、愛的團契。我的本性和信仰與其他人(即受造物和天主的兒女)是有關聯的。作為好的管理人–一名看守人和行政人員–我必須好好地照顧我的生命和健康。所以,要當好的管理人,在一般情況下,便要積極地照顧自己的整個身體及其所有器官;而反面的角度便是不該毀傷自己的身體或任何健康的部位或器官。但鑒於特殊情況,好比對基本健康已構成障礙,切割或移除某器官是允許的:例如切除壞疽的脚;一切也是為了整體的生命和健康(自體造型的移植也需道德地遵守整體原理)為大前提。
若以身體作為整體而言,倫理學家會區分為解剖完整性和功能完整性。解剖完整性即身體的所有器官都受到尊重–身體完整;而功能完整性即身體的功能受到尊重–有效的身體功能。解剖完整性有別於功能完整性,要過基本健康的生活是需要功能完整性;而解剖完整性可沒此顧慮。因此,功能完整性是要付上道德責任的,也就是說:『這是決定活人在移植上的道德問題關鍵因素』(作者引用Benedict M Ashley, OP and Kevin D. O’Rourke, OP) 。一個很好的例子:移除一個腎臟是不會嚴重損害身體的基本功能,單靠一個健康的腎臟便能過正常生活;所以不需要第二個腎臟『去證明個人身份或生育身份,至於功能完整性對腎功能衰竭或高血壓的長期風險亦較低』(生物倫理學家Angeles Tan Alora, MD)。故此,天主教教理(CCC,2296條)這樣寫:「若為了延緩他人的死亡,而直接引發另一個人的傷殘,或者死亡,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
不是所有器官也可以移植的,例外的有大腦和生殖腺, 它們分別與人的個人身份(大腦)和生育身份(生殖腺)有關,都是因為[人的獨特性]和[醫護界竭盡所能去尊重和保障]的原則(新修訂的《醫護人員憲章》)。
捐出一個腎,我做得到,但我實在沒義務這樣做。這並不是一個義德的問題——即使捐獻者有可能是親屬關係——是團結或愛德的問題,這對我來說比去除我的腎臟可能涉及的輕微風險來得更重要。這個器官對捐獻者、接受捐獻者和整個人類都是良好和有益的事,是一份自由而慷慨的禮物。聖若望保祿二世認為器官捐獻是一種勇敢分享的行為。
第二個問題是:我或你,在捐贈器官時,是有需要提供知情同意的嗎?器官捐獻者是必須具備自由和知情的同意。為了能夠做到這一點,身為捐贈者的我,是應該對獲取器官者有充分和真實的了解、醫療手術可能做成的影響、和涉及捐贈後對生命或健康帶來的後果和問題。
- 器官捐贈:接受捐贈者
第一個要作答的問題是:捐出的腎臟對接受捐贈者是有利的嗎?腎臟移植,或其他器官移植,似乎是有益的,只要:是沒有更好的治療選擇;移植的好處大於接受者所要承受的負擔和風險;接收的腎臟與接受者的身體是相互兼容的;對器官的接受者來說,如果擁有一個優良的預後報告等等。
第二個要面對的問題是:接受捐獻者是否享有自由去同意器官的移植?接受捐獻者給的知情同意是應該在得到適當的通知、並在清晰了解被提供的資訊後作出的決定。
還有一重要問題:誰應該接受這些待移植的器官?在相關受惠者並不存在重大的道德問題;如捐贈者可以選擇把這禮物送給哪個受惠者,而彼此也不是直系親屬的話,應該沒什麼大的問題,但如果器官是捐贈給某中心或某公立醫院,然後把這些待移植的器官,再另行分配時,問題就出現了,在移植的器官上的分配,可能會牽涉法律和道德問題。
鑑於器官的稀缺和等侯接受移植者的長長名單,誰應該得到某器官:是我團體的成員?是我國公民?還是來自另一個國家的公民?我們應該照顧本地的人?還是照顧國界的腎臟待移植受惠者?甚至不分國界?當中有主張無邊界的、有堅持要國界限制的、也有贊成區域邊界的(雖然不是完全),例如北歐的國家。雖然最理想的是無國界,但也可能會贊成部分開放的國界有利外國人:仁愛始於家,但不應止於此……這是很多國家目前採用的政策,包括澳門在內。
最重要的:便是不論在國家、在區域、或有世界社會公正的地方,都不該因族裔、宗教、性別、年齡或社會經濟因素而有所歧視。任何國家的公民,在權益和尊嚴方面基本都是平等的,因此必須得到平等待遇……平等個案便應得到平等待遇!
誰才是最佳接受器官的的人(醫療效用)?誰才是有需要人士中最有需要的?需要和治療準則都有助於決定誰該受贈。又是否需要遵守常態這種規則,例如[先到先得]?用抽籤的方法可行嗎?無論如何,應先考慮利益和負擔的公平分配作為配送的道德原則。還有一點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有關部門在經過適當的公開討論後,才立下標準和政策,如何去分配器官。
我們用若望保祿二世(2000年8月29日)一則富啟發性的文本作結束:「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在分配捐贈器官時,要抱着一個明顯的道德原則:絕不應具有[歧視性](即不該因年齡、性別、種族、宗教、社會地位等等而有所影響;或偏袒[功利],(即基於其工作能力、對社會之價值等)。 相反,在決定誰應優先接受器官時,應根據免疫學和臨床因素作出判斷。任何其他標準都只是表明這決定是武斷和主觀的,更不會考慮每個人的內在價值,故不應被任何外部環境干預。」

 Follow
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