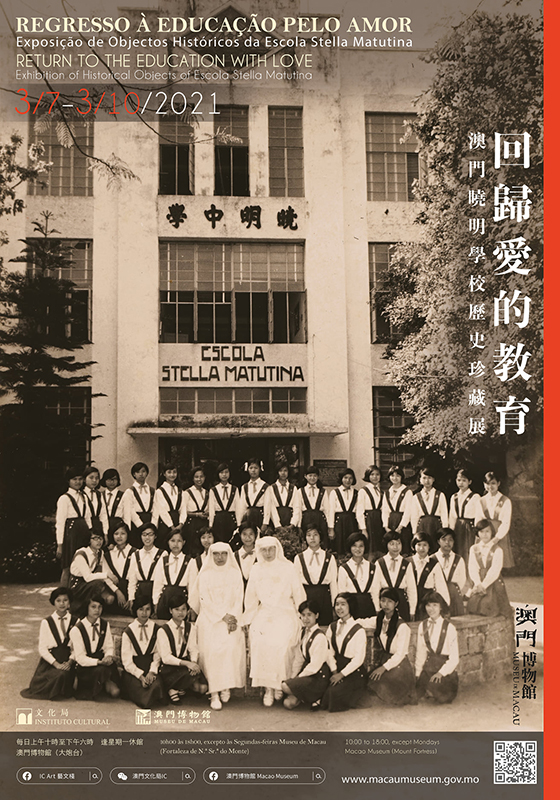慈悲的面容(Misericordiae Vultus)
教宗方濟各
信訊 恭譯
14. 朝聖乃這聖年的特別記號,因為這是每個人的人生之旅的圖像。人生就是一次朝聖,人類就是個「viator」(旅客),是個走在通向他想到達的目的地的路上的朝聖者。同樣,到達在羅馬的或別處的聖門,每個人都要,按各自的能力,踏上的一趟朝聖之旅。這要成為一個記號,指出仁慈是個要到達的目的,而且需要投身和犧牲。那麼,願這趟朝聖成為皈依的酵素:透過跨越聖門,我們將讓我們自己被天主的仁慈所擁抱,我們也將對別人仁慈,就如天父一直如何對我們一樣。
主耶穌指出了藉以能達到其目的地的朝聖不同階段:「你們不要裁判人,就必不被裁判;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必不被定罪;你們要寬恕人,就必得寬恕。你們要施與人,就必有施與你們的,並用十足的量器,壓實、滿得溢出來的,倒進你們的懷裏。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要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路6:37-38)。他說的首要是不去裁判別人和不去定別人的罪。如果任何人不想惹來天主的裁判,他就不能成為自己的弟兄姊妹的裁判官。人類,的確,他們的裁判只停留在表面,但天父卻看內在。由嫉妒而生的說話何其壞!在一個人的弟兄姊妹不在時說他壞話,就等同蓄意破壞他的形象,危及他的名譽,並任由他受流言蜚語的傷害。從正面的角度看,不去裁判別人和不去定別人的罪,就是去瞭解每個人的好處,並讓他免受我們的局部而不完全的判斷和我們自以為無所不知的假設之苦,但作為表達出仁慈來說,這仍未足夠。耶穌也要求你們去寬恕和去給予。我們要成為寬恕的工具,因為我們從天主那裏獲得了寬恕在先。要對所有人大方,因為我們知道天主十分大方地把祂的恩寵傾注在我們身上。
因此,好像天父般仁慈,就是這聖年的「座右銘」(motto)。在仁慈中,我們可找到天主如何去愛的證據。祂把祂的整個自己給予我們,永遠的,無償的,並沒要求任何回報。每當我們呼喚祂時,祂都來幫助我們。教會每天的祈禱(譯按:即時辰頌禱禮,或稱大日課)以這句話來開始,真是美好:「天主快來拯救我,上主速來扶助我」(詠70:2)。我們所呼喚的這份援助,就已是天主對我們的仁慈的第一步。祂來拯救我們在其中生活的這軟弱的狀態。這份援助就是使我們抓緊祂的臨在和祂的親近。日復一日,在被祂的憐憫不斷觸動之後,我們也能變得對所有人都有憐憫之心。
15. 在這聖年中,我們可去經驗一下,向生活於生存環境最邊緣的人──這些往往是現代世界自己創造出來的──敞開心懷。在今天的世界中,不安定的狀況和痛苦何其多!刻在那些因著富人冷漠的無動於衷而聲嘶力竭的人的血肉上的傷口又何其多!在這禧年中,教會尤其被呼召去治療這些傷口,去為它們傅上撫慰之油,去以仁慈來包紮它們,並以團結一致和他們應得的注意來治療它們。讓我們不要陷於那使人蒙羞的冷漠和無動於衷,陷於那麻木人的心思而使之無法發掘新意的習以為常和見慣不怪(意:abitudinarietà),也不要陷於那極具破壞力的犬儒主義(意:cinismo【譯註1】)之中。讓我們打開雙眼,去看看世間的痛苦,去看看這麼多失去尊嚴的弟兄姊妹們的傷口,讓我們在聽到他們求救的呼聲時感到激動。讓我們緊握他們雙手,讓我們支持他們,並讓他們感受到我們的臨在、友誼和手足之情的溫暖。願他們的哭訴也成為我們的哭訴,並讓我們一起打破那冷漠的樊籬,這掩飾我們的虛偽和自私的樊籬已勝利得太多了。
我誠切的渴望,在這禧年中,基督徒省思一下靈性上和身體上的仁慈事工。這是重新喚醒我們那在貧窮的悲劇面前昏睡已久的良知並日益深入到那窮人乃天主仁慈的優先的福音中心的方法之一。耶穌的宣講說明了這些事工,為使我們可知道自己有否以祂門徒的身份生活。讓我們重新發現這些身體上的仁慈事工:給予饑餓者食物、給予口渴者飲品、去給赤身裸體者衣穿、招待異鄉人、協助病人、探訪囚徒、埋葬死者。讓我們也不要忘記那些靈性上的仁慈事工:向有疑惑者提供建議、教導無知者、勸誡罪人、撫慰受苦者、寬恕過犯、耐心忍受那些討厭的人,以及為生者死者而向天主祈禱。
我們無法躲過主的說話,並將基於它們而被審判:我們可曾給予饑餓者食物、口渴者飲品?我們可曾招待異鄉人,又可曾給赤身裸體者衣穿?我們可曾花時間在病人和囚徒身上(見瑪25:31-45)?同樣,我們會被問到,我們可曾開解那使人墮進恐懼之中的並常是孤獨之源的疑慮之心?我們可曾使上百萬活於無知中的人克勝無知,尤其是那些被剝奪了離開貧窮所需的援助的孩童?我們可曾寬恕過那些冒犯我們的人,並拒絕那最終會帶來暴力的所有形式的忿怒和仇恨?我們可曾跟隨那對我們如此有耐心的天主的榜樣,同樣的待人耐心?最後,我們又可曾在祈禱中把我們的弟兄姊妹交託給主?在每個這些「弱小的人」中的,都是基督本人。祂的肉身再次以備受折磨的、受了傷的、受盡鞭撻的、營養不良的、正在逃難的身體上,以求我們認出、觸摸和細心照顧。讓我們不要忘記聖十字若望的說話:「在人生的黃昏時,我們將基於愛的準則而被審判」。
16. 在《路加福音》中,我們找到以信仰來活出這禧年的另一重要方向。聖史敘述耶穌,在一個安息日中,回到納匝肋,一如他習慣做的,他進了那裏的猶太會堂。他們叫他朗讀聖經並作出評注。那段經文就是依撒意亞寫到下面段落的地方:「上主的神已在我身上,因為祂已為我傅了油,並派遣了我去把喜訊帶給貧窮的人,去向俘虜宣告釋放和向盲人宣告復明,去使備受壓迫者得到自由,去宣講上主的恩慈之年」(61:1-2)。「一個仁慈之年」:這就是主所宣佈的,也是我們想要活出的。這聖年所附帶的,就是在這位先知的說話中迴響著的耶穌使命的豐盛,去把撫慰的說話和態度帶給貧窮的人,去向那些現代社會新奴隸制度下的囚徒宣告釋放,向使那些失明的人看出他們何以陷於如斯境地,去使那些被剝奪尊嚴的人重獲尊嚴。藉基督徒見證被召喚去給予的信仰回應,耶穌的宣講將重現眼前。願保祿宗徒的說話與我們常隨不離:「行仁慈者,喜樂行之」(見羅12:8)。

【譯註1】「cynicism」(希:κυνισμός=kynismos=犬儒主義)一詞,早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已出現,今天仍為不少報刊評論員所用,唯古今意義不大相同。
犬儒主義本指主前六世紀末始冒地一個古希臘哲學派系。犬儒士(Cynics;希:Κυνικοί=Kynikoi;拉:Cynici)認為,人生的目的,在於活出與自然一致的美德。既為理性思考的動物,人類自能藉嚴謹的訓練和藉以一種對人類來說是自然的生活方式來達致幸福的境界,並拒絕一切古希臘羅馬社會傳統上對財富、性愛以及名氣的追求。相反,他們度一無所有、身無分文的清簡生活。此主義這名字,哲學史家相信,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的人認為他們就此擯棄社會一直推崇的價值而鄙視他們,故稱其為「像狗一樣的」(希:κυνικός (kynikos)=dog-like)。
時至今日,非哲學上的,在日常生活的語境中,犬儒主義成了指一種心態,因著相信人類本質上就是自私的,受情緒所控,並深受人類在農業生活和文明未建立之前的求生本能所影響,因而普遍地對別人的動機,尤其是行好事或宣講道德的動機,多抱執疑不信的心態(見Navia, 1996)。一個抱犬儒心態的人,普遍對人類或對那些為了抱負、渴望、貪心、自我滿足、物質主義、人生目標或看法主張等無論好壞但犬儒者都認為是虛妄的、不可達到的,或最終都無意義的動機而行事的沒有信心甚至不懷希望,並認為他們都而因而應受到嘲笑或勸止。順帶一提,不少人會把犬儒主義與另一個相近但不相同的心態──懷疑主義(skepticism)──混淆起來。簡言之,懷疑主義認為真正的知識是不可能達到的,道德價值是主觀的、相對的;而犬儒主義,由於是對人性的不信任,甚至不懷任何希望,因而顯得對一切都覺得無所謂,或冷漠、袖手旁觀。
由於文中沒有言明,因此我無法斬釘截鐵地說教宗所指的犬儒主義究竟是古義或今義。但從第十五條的上文下理來說,大概是指後者。

 Follow
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