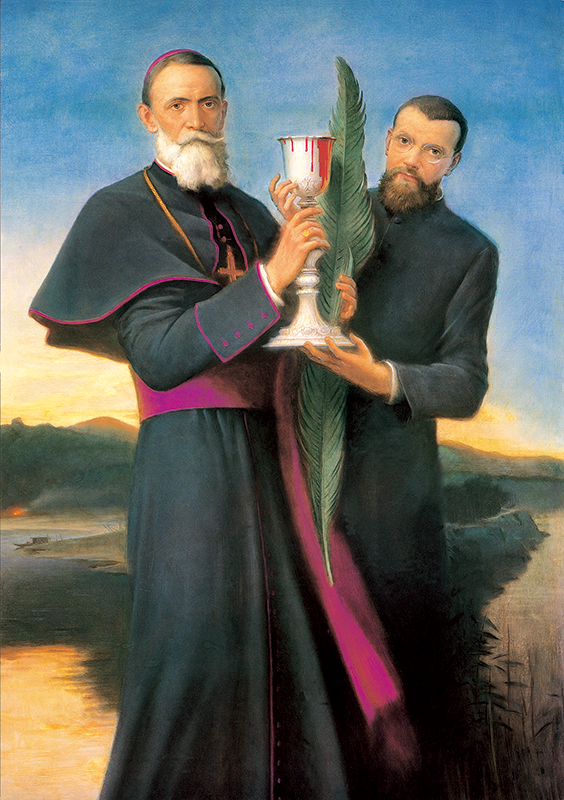文:Edward Pentin
教廷禮儀及聖事薩拉樞機因年屆75歲,今年二月向教宗方濟各請辭並獲接納。薩拉樞機早前接受意大利媒體訪問,透露對於禮儀的一些意識上鬥爭,為自己帶來「極大的痛苦」。
薩拉樞機早前接受意大利媒體《Italian daily Il Foglio》的記者Matteo Matzuzzi專訪,指在今時今日的教會中,我們常常表現得好像是政治、權力的問題,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強行帶來的影響,完全打破傳統,甚至與傳統產生矛盾。
他認為,解決方案是,讓教會從彌撒開始,藉着面朝東方(ad orientem),讓天主放回禮儀的中心:「若天主不是教會生活的中心,那教會便會面臨死亡的危險。」他暗示教會「目前正經歷『基督受難日』」,卻補充「基督的勝利是來自苦難的十字架。」
薩拉樞機強調,將此類議題視為意識形態上的問題並不合理:「我不認為新派與保守派之間的議論,在教會中有任何意義。」他補充說:「這些分類是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教會並不是政治鬥爭的場所。」在訪問中,他還提到自己與教宗方濟各與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之間的關係;在他任內,他對未來的計劃,並對教會未來數年的看法。
樞機閣下,很多人對您辭任教廷禮儀及聖事部一職感到意外。這個時候辭任意味着甚麼呢?
如所有的樞機一樣,按一向的規矩,在去年六月我75歲生日的情況下,我向教宗遞上我的辭呈,辭去教廷禮儀及聖事部部長一職。當時,他請求我繼續我在教會內工作直至其他決定。然而,他早前告訴我接受我的辭呈,我對他的決定立即表示高興及感恩。
我經常說:順從教宗不只是人類層面上必需的,也意味着遵照基督的旨意,因耶穌基督任命伯多祿宗徒及其繼任人帶領教會,成為教會的領導者。
我曾服務三任教宗——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本篤十六世及教宗方濟各——在羅馬教廷服務超過20年,對此我感到很高興及自豪。我盡力去成為福音真理的忠實、順從與謙遜的僕人,縱使有許多記者不時重複相同無意思的話題,我從來沒有反對過任何一位教宗。
在禮儀及聖事部20年的服務中,您學到了甚麼?
有些人認為這部門是一個充滿榮譽的地方,但沒有很大的重要性。相反,我深信我們對禮儀的責任,讓我們放置在教會的中心,教會存在的目的(of her raison d’être)。教會既不是一個行政機關,也不是一個人類的機構。教會奧秘地延長基督在這世上的臨在。正如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中所指,「禮儀是教會行動所趨向的頂峰,同時也是教會一切力量的泉源。」(《禮儀》憲章,10)同時,「因為[禮儀]是基督司祭及其身體——教會——的行為,禮儀是一個卓越的神聖行為;教會的任何其他行為,都不能以同等名義,和禮儀的效用相比。」(參閱《禮儀》憲章,7)
教會的存在,就是要將人類奉獻給天主,同時將天主帶到眾人當中。這亦是禮儀的角色:去朝拜天主,同時將天主的恩寵傳到眾靈魂。當一個禮儀「生病了」,整個教會都會陷入危機,因為她(教會)與天主的關係不單止削弱了,而是損壞了。
現實中有許多有關教會的言論,指教會有必要改革,我對此感到驚訝。但是,我們(教會)是宣講有關天主[的事情]嗎?我們是宣講救贖工程嗎?這救贖工程也就是基督主要透過他神聖的苦難、他從陰府的復活,以及他光榮的升天,這逾越奧跡「以聖死摧毀了我們的死亡,並以復活恢復了我們的生命」。(《禮儀》憲章,5)與其談論我們自己,倒不如讓我們轉向天主!這是我多年來一直所強調的訊息。若天主不是教會生命的中心,那教會便面臨死亡的危機。那正正為何教宗本篤十六世所指,教會的危機基本上是禮儀的危機,因為也就是與天主關係上的危機。
這也是為何我緊隨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理念,堅持:禮儀的目的並不是為團體或人類而辦,而是天主。這一點能在『面朝東方』(ad orientem)的禮儀中,很好地展現出來。教宗本篤十六世說:「若不可能面朝東方時,十字苦像可作為我們內在信德的方向。十字苦像必須放在祭台的中心,也要成為司鐸和參禮團體目光的中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遵從教會傳統的邀請、向聖體開放:Conversi ad Dominum(意即:轉向天主)。然後,我們轉向那位藉死亡而帶給我們永生,轉向那位在天父前支持我們、將我們抱入他的懷中,並使我們成為活着的人,成為聖神的宮殿(參閱格前6:19)。」當每個人都朝向十字苦像時,我們避免了人性上的接觸,並專注於禮儀中;我們向天主傾注的恩寵開放。「在禮儀中,司祭與信友面朝對方,這僅出現在當代的基督宗教中,這與傳統的基督宗教完全不同。可以肯定的是,司祭和信友並不是彼此對向着祈禱,但是向着天主。」在靜默中,基督親自來與我們相遇。(參閱《禮儀的神學》教宗本篤十六世)這也是為何我重複堅持禮儀要回到沉默。當人保持靜默,便會為天主留一個地方。相反,當禮儀變得許多言語時,便會忘記十字架就是禮儀的中心,只會圍繞着麥克風等外在因素。這一切都是重要的,因為他們決定我們給天主預備的地方。不幸地,這些問題都變成一些意識上的問題。
你似乎在表示遺憾。您事實上想指甚麼呢?您所說的「意識上」是甚麼意思呢?
今天在教會中,我們常常表現得好像是政治、權力的問題,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強行帶來的影響,完全打破傳統,甚至與傳統產生矛盾。目睹這些「鬥爭」,為我來說是極大的痛苦。當我提到禮儀中面朝東方及神聖性的層面時,我被告知:「你正在反對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這是錯的,我不認為新派與保守派之間的議論,在教會中有任何的意義。這些分類是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教會並不是政治鬥爭的場所。唯一重要的,是更深入地尋求上主,[在禮儀中]謙遜地下跪並與天主會面。
當教宗方濟各任命我時,給了我兩項指示:一、執行梵二《禮儀》憲章;和二、將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對禮儀的教導活出來、應用出來。我堅信這兩個指示,都是往同一個方向的。的確,教宗本篤十六世是對梵二理解最深的人,繼續他的禮儀工作,最佳方法就是執行梵二大公會議的本身。不幸地,一些思想家希望將梵二前的教會,與梵二後的教會分隔,產生對立。這些人,就是教會的分裂者;他們所做的,是魔鬼的工作。教會是唯一的,沒有破裂、沒有改變路線的教會,因為教會的創辦者耶穌基督,昔在,今在,永在(參閱希13:8)。教會本身朝向天主,而教會亦帶領着我們(信友)朝向天主。透過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從聖伯多祿到教宗方濟各這條信德的宣認上,教會使我們轉向基督。
基於禮儀本身就是神聖的特質,為禮儀騰出靜默的空間,甚至[司鐸]間中面朝東方主持彌撒,正如教宗方濟各在西絲汀小堂或在洛雷托朝聖地般,都是滿全梵二的精神。
有一件非凡的巧合事件:在我宣布離任當天,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給我一份有關他對禮儀方面的作品的法文版本。其中,我看到他回應天主的旨意,去透過他的作品,恢復一個能讓天主重返教會生命核心的禮儀精神。
待續

 Follow
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