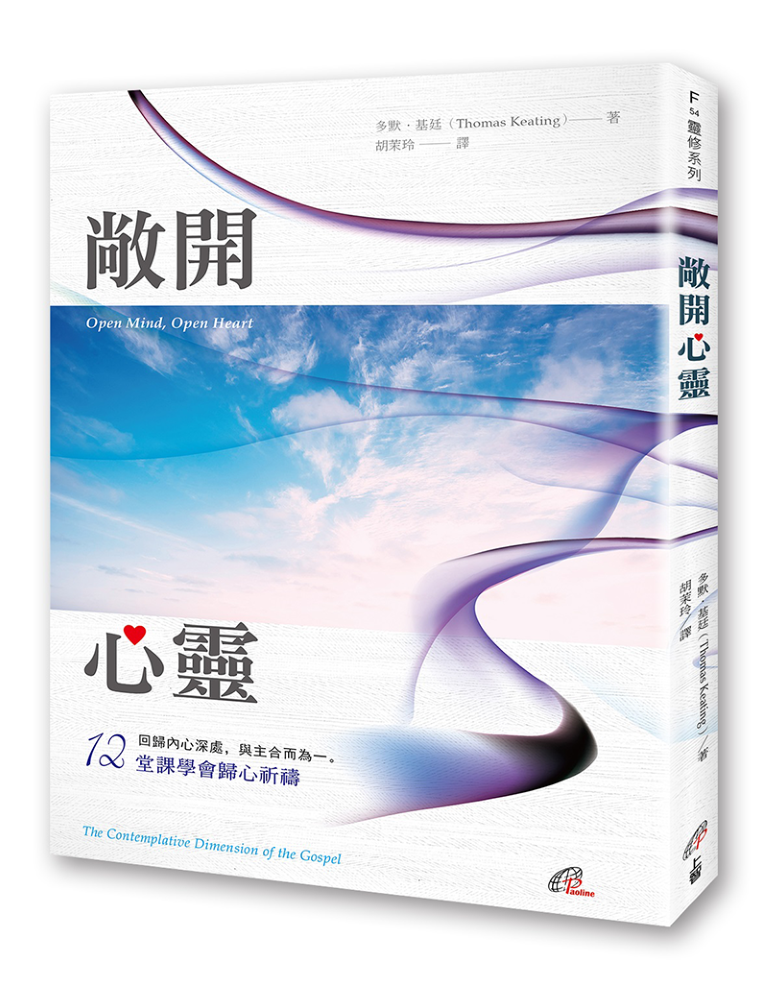文:姚子汶
金邦尼傳教士歐衛道神父上月接受本報訪問,簡單介紹有關他博士論文的「景教」研究。「景教」可算是基督宗教踏足中國的憑證,但多年後的今天,並非人人認識基督宗教,不少華人仍對基督宗教不感興趣。作為一名來華已久的傳教士,歐神父亦發現這個現象。在長達兩小時的訪談中,歐神父除了分享論文的成果外,也分享他多年來在華人地區傳教的挑戰與心得。
為何你選擇「景教」作為你論文的題目呢?
當我在香港任教時,我準備了三個協士論文的方案,分別是「亞歷山大里亞學派」、「聖師、教父濟利祿主教的教理」和「中國的奈斯多利派傳教士」。在得到耶穌會士的Henryk Pietras教授指導後,他道出前兩個題目之人物,是向與自己擁有相同國籍的人宣講,唯獨奈斯多利派是敘利亞傳教士並向中國人宣講,此啟發了我。教授對我說:「這應是一名傳教士的工作,就如你一樣。」這也是個事實,令我決定花三年時間專注在「景教」與「基督宗教」的研究上。
在整個研究中,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
最困難的地方,就是要做資料搜集時的方式,同時要令你的作品富有原創性。一份博士論文應是一些對科學研究的一些嶄新認知,例如:新的提議、新的方法、新的見解、新的解讀等等。為我的論文中,對兩份手稿整理、組織和研究的方式都是原有的,加上當中的解讀和所闡釋的重點,也算是原有的。另外,能夠得到著名神學家、教父學家與歷史學家Henryk Pietras 教授,漢學家及景教與中國基督宗教歷史研究學者Matteo Nicolini-Zani教授的指導,是我莫大的榮幸,亦因此能獲得這最佳論文的殊榮。
你的論文提及「景教」傳入中國。在這裡,讓我聯想起到中國及其他東方地區的「傳教士」。作為一名傳教士,你認為最具挑戰性及最困難的是甚麼?是語文嗎?
學習語文是其中一個最具挑戰的方面,但語文只是整個文化的其中一項,懂得一個語文不代表懂得整個文化。文化還包括歷史、宗教、傳統、習俗等⋯⋯我懂中文不等於我認識中國,這是不正確的;我認識中文,但不代表我認識中國文化。我在這堂區(勞工主保堂)服務好幾年,也在這堂區生活很多年。期間,我在這裡主持主日彌撒、教慕道班,及後又在香港聖神修院任教,接觸了不少的人。當你接觸更多的本地人,才能真正認識這裡的文化。
猶記得起初到這裡教慕道班時,慕道者最後離開、不繼續慕道,其中一個原因是不理解我所表達的。語言是其中一個問題,但後來其中兩名離開的慕道者最後也領洗,這讓我明白到,作為一名傳教士是需要尊重他們的背景與傳統,亦要尊重他們消化的時間,曾經有一名朋友,他最後不繼續慕道,是因為他家裡的傳統;我們在這方面也要尊重。
我在哥斯達黎加出生,在拉丁美洲成長及生活超過20年,然後我在歐洲讀書長達九年,及後我花了20多年的時間在亞洲;這三大板塊的文化完全截然不同。我不能將拉丁美洲的方式,套入亞洲這裡,是完全行不通、是不正確的。每個地方的歷史及傳統,都會影響着各地方的生活與處事方式,所以傳教時也要平衡這方面,但本地化的同時,亦不能妥協一些會違反我們宗教的原則。譬如:某些文化傳統及習俗需要活人祭祀;但我們的宗教是不能接受及妥協的。
學習一個地方的文化需要很多年的時間,否則我們只是將西方文化及思想,移植到這個地方使用罷了。這為一名傳教士來說,是最困難及最具挑戰性的了。傳教士也是外國人,對於一個新地方語言的認知是非常有限,再加上要了解這地方的文化,這為傳教士來說,就是最有挑戰性的了。
你如何評價中國的思想呢?會否覺得中國人的思維,沒有西方人的開放?
要作出對比誰是較開方,兩者是不對等的。例如,我在修院教授一些很深奧與複雜的課題,問學生有沒有任何問題,總是無人回應。我當時心想,這怎麼可能!作為一名老師,學生沒有問題的可能性只有兩個:一、老師解釋得非常清楚;二、學生根本完全不明白老師所說的。但後來數年的經驗中,我慢慢發現,是需要鼓勵這裡的學生去發問,所以我請他們把問題寫下。最後,我的電郵總會收到許多學生的問題,有些學生更有十幾條問題!所以,這是很重要的,每個地方的人的思維都不同,但要以合適的方式與他們溝通。
你剛說到有關傳統與思維。在中國人的思維中,我們經常認為「神」是高不可攀的。為你而言,要如何向一名中國人深信而且心中感受到,天主聖父就是一名慈父呢?
神學的方式有兩種:「肯定神學(Kataphatic theology)」和「否定神學(Apophatic theology)」。拉丁教會用的是「肯定神學」,即是需要嘗試解釋天主、解釋這個奧秘。而東方教會使用的,則是「否定神學」,就是不用解釋天主,只需帶進默觀祈禱,天主自有方式啟示給你。我認為,亞洲人的思維是傾向「否定神學」的方式,而我們的教理則是以「肯定神學」的方式,所以當中可能存有差異。
在我的觀察中,有時會是一個限制。我們外表與行為上會相信天主是我們的父親,但我們的內心,可能仍會疑問「天主怎可能是我們的父親」,這可能因為「父親」是一個概念,又或因為各人對「父親」的背景有所不同,導致難以將「父親」與「天主」劃上等號。
為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始終會有一種想法,基督宗教不是屬於中國的宗教,是一個西方傳入的宗教。你對此有何看法?這種看法會影響我們接受真理嗎?會影響我們傳福音的工作嗎?
我有很多非基督徒的中國朋友,經常會有此情況出現。他們會說:「基督宗教是你們這些白皮膚的西方人的宗教,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宗教。」我也曾有此想法,為何普遍中國人會有此刻板印象呢。在我們的認知裡,我們知道福音是為所有的人,不分種族、無分彼此;但為非教友的人來說,他們並不覺得,而且這想法根深蒂固。我認為,只有我們讓福音更「亞洲化」,甚至更「中國化」,才有可能令大部分中國人除去這種刻板印象,這也是我在過去數年在做的工作之一。

 Follow
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