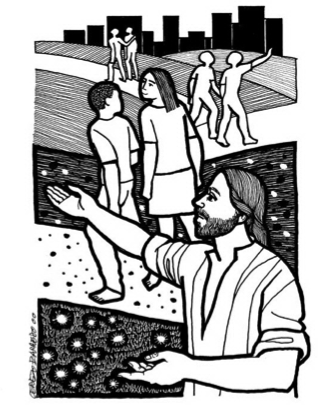陸達誠神父
紐曼樞機(1801-1891)原是聖公會牧師,1845年皈依天主教,二年後晉鐸。1851-1858年應聘為愛爾蘭天主教大學校長,發表《大學的理念》這本教育經典之作,書中提及「紳士」的觀念。
樞機除了七、八年在愛爾蘭當校長外,此前此後一生大部份時間生活在有「英國雅典」之稱的牛津。交往的朋友都是學富五車,幽默風趣的英國紳士。可以想像這一群志同道合學者組成的教授團體是多麼的饒富樂趣。紐曼對大學的理念在牛津開始萌現。他的紳士觀也來自牛津的生活經驗。他的「紳士」即智者,既有學識又有學養。他說:
「紳士決不做加給別人痛苦的事。他所關切的事是除去使他的鄰人不能自由自在地行動的阻礙。他巴不得他們都感到在家一般的舒適。他密切注意著他的同伴們的性格和需要:對害羞的人特別溫柔,對處在團體邊緣的人顯示溫良,對別人荒謬的行為表示寬容;他能專心地與人談話,避免不適當的暗示,或令人不悅的話題;在談話時不鶴立雞群般地突出,也從不顯出疲憊。除非不得不說,他從不談自己,不反擊式地為自己辨護。對毀謗或八卦毫無興趣。他不輕易地判斷干擾自己者的動機,卻從正面的角度解釋事故。在討論有爭議性的話題時,他不會卑鄙小氣,不佔取不合適的便宜。在辯論時不誤解正人君子,不尖銳刻薄,或暗示一些難以啟口的損人的話。他從寬廣的角度遠視古哲的箴言:「我們面對及回應敵人時,要想有一天他可能成為我的朋友」。別人凌辱他時,他寬容以待;受人中傷,無暇記憶;對怨恨,懶得回應。有關哲學的原則,他能忍耐別人的見解,寬大為懷,不執著自己的想法。無法避免的痛苦,無法挽回的親人亡故,命定的死亡,他一一接受。他知道人類理性的脆弱,亦知其威力、影嚮範圍和局限。如果他無信仰,他的深沉的修養和廣闊的視野不會讓他嘲笑宗教或刻意反對之。他聰明得不會傾向獨斷或對自己的不忠著迷。他與宗教寬容為友,他這樣做並非只因為他的哲學指示他應該公正地面對信仰的差異,更因紳士身份和溫柔的氣質驅使,而這些都是文明人的本色。」
紳士如此,紳士的團體亦然。在同書中,紐曼如此詮釋「大學」:
「一個飽學之士的團體,每一位成員熱中於自己的專業,又是相互競爭的對象。他們或因友誼或因知性的接近,相聚在一起調節他們研究的不同主題間的主張和關係。藉此,他們學習尊敬別人,樂意向別人討教,並相互協助。」
英國作家紀律 (Sheridan Gilley) 批判紐曼,認為紐曼此文所持的是一般智士的立場,而非基督徒立場。他的紳士觀不由信仰而由文明 (civilization) 所生。筆者認為紐曼的信仰有其過程,而他對智者的洞見恰好可協助我們把一般智者的想法當作起點,逐漸引渡到信仰的智者那裏去。
若紐曼的紳士觀不甚全合信仰的智者觀,至少點出了英國學者對智者的看法。紐曼的智者觀與孔子的君子觀若合符節。可見東西方世界在沒有直接交流的時代,已有超越時空的共識。不過紀律先生說得對:討論宗教智者,不能停留在紳士的階段,因為宗教有不同的,或許更高的要求。
【參考】1. 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ed. T. Ker.
2. Sheridan Gilley, “What has Athens to do with Jerusalem? Newman, Wisdom and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see Where shall Wisdom be found? Ed. Stephen Barton, (Edinburgh: T&T Clark, 2005)

 Follow
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