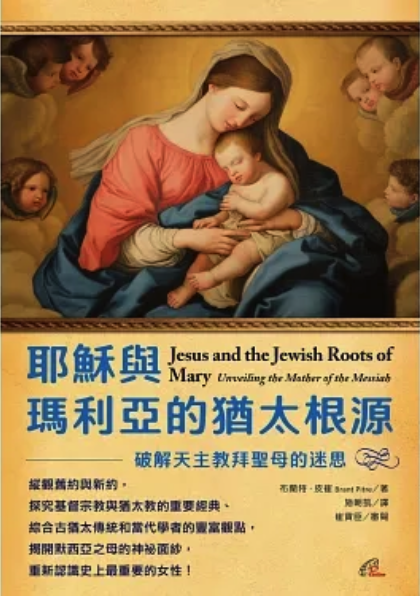羅伯特•薩拉樞機
聖座禮儀聖事部部長
丙、《禮儀憲章》頒佈後,發生了甚麼事?
我之所以提出,應該重新檢視《禮儀憲章》及其後的改革,是因為我不認為,我們今天可以坦誠光看《禮儀憲章》的首節,便大家自滿已達成了它的各項目標。我的兄弟姊妹們,會議教長們所提到的信徒們,去了那裡?眾多的信徒們,今天已經變成了無信者:他們根本已經不再來參與禮儀了。引用聖若望保祿二世的話:「忘記天主令人放棄人類。
因此,難怪今天日常生活,已大為開放給毫無限制的哲學懷疑論、價值觀與道德的相對主義、實用主義、甚至乎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歐洲文化予人『靜默背教』的印象,使人以為自己可以完全自給自足地生活,猶如天主不存在一樣。」(《教會在歐洲》宗座勸諭 2003年6月28日,9節)大公會議所追求的合一,去了那裡?我們仍未達成合一。我們已召叫到全人類加入教會的家庭裡,取得真實的進展嗎?我就不敢苟同了。可是,我們卻對禮儀,做了極多的事!
在我晉鐸四十七年及三十六年主教牧職生涯中,我可以確認,不少公教團體及個人,確實能夠在梵二會議之後改革的禮儀之中,熱情與歡樂地生活和祈禱,獲取了很多,就算不是全部,會議教長們所渴求的善果。這是梵二會議一個極大的果效。不過,按我的經驗,我亦知道—現在我身為是禮儀聖事部部長—今天教會上下,禮儀被重重扭曲,而且很多情況其實是可以改善,致使大公會議的目的,得以達成。在我思量一些可行的改良措施之前,讓我們首先反思一下,《禮儀憲章》頒布後,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十六世紀時,當時的教宗,把特倫多大公會議所尋求的禮儀改革,交託給一個特殊委員會手中,以編纂禮儀書的修訂本,供教宗日後公佈。這是一個完全正常的程序,而真福保祿六世沿襲這個程序,於1964年成立禮儀憲章執行委員會 (Consilium ad exsequendam constitutionem de sacra liturgia)。因着委員會秘書,步毅尼總主教 (Annibale Bugnini) 所出版的回憶錄 (The Reform of the Liturgy: 1948-1975, Liturgical Press, Collegeville 1990),我們對這個委員會,認識匪淺。
委員會落實《禮儀憲章》的工作,肯定受到《禮儀憲章》以外的勢力、意識形態、和新建議所影響。例如,即使大公會議並未提出引入全新的感恩經,這個意見卻出現了,並且被採納,而這些新的經文,也被教宗權威地公佈了。步毅尼總主教自己也明言,有一些經文和儀式,是根據當代的風氣撰寫或變更的;這包括合一運動思緒的考量。我們必須研究,到底當時的所作所為,是否過猶不及;又或者,是否真的有助達成《禮儀憲章》的目標,而非阻礙其達成。我樂見今天的學者,深入地研究這些事項。儘管如此,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真福保祿六世,的確判斷了委員會所提出的改革為合適,進而公佈。他運用了自己的宗座權威,使改革變成了規範,同時又保證了其合法和有效地位。
不過,改革的官方工作進行之際,一些對禮儀非常嚴重的誤解逐漸浮現,並且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這些對神聖禮儀的妄為,受生於一種對大公會議的錯誤理解,導致禮儀慶典,流於主觀,注重個別團體的訴求,而非對全能天主的祭獻朝拜。我在禮儀聖事部的前任者,阿林澤樞機 (Francis Cardinal Arinze),就曾把這東西,稱為「自助彌撒」(“the do-it-yourself Mass”)。就連聖若望保祿亦不得不在其通諭《活於感恩祭的教會》(2003年4月17日)中寫道:
「教會的訓導當局致力於宣講聖體奧蹟,在基督徒團體中相對有了內在的成長。當然,大公會議所開始實施的禮儀改革,也大大有助於信友更有意識、更積極、更有效果地參與聖祭。在許多地方,朝拜聖體也是一個重要的每日敬禮,而且成為成聖的無盡泉源。信友在基督聖體聖血節時虔誠地參與聖體遊行,是天主所賜的恩寵,每年都能給參加的人帶來喜樂。
對聖體聖事的信德與愛德,還有許多正面標記,也都頗值一提。可惜的是,跟著這些光明面而來的,也有一些陰暗面。有些地方幾乎完全廢除了朝拜聖體的敬禮:教會的許多方面都曾有陋習發生,使教友對於這奇妙聖事的健全信仰以及天主教教義感到困惑:有時我們會遇到極度貶低對聖體奧蹟的了解的情況。例如把感恩聖祭中犧牲祭獻的意義除去,只當做一種友愛的盛筵來慶祝。更有甚者,從宗徒傳下來的公務司祭職,其必要性有時卻被遮掩,聖體聖事的聖事性質也眨為只有宣講的功效而已。這使得許多地方的合一運動,儘管有好的意向,卻用違反教會對信仰表達的方式,來舉行聖祭,而且樂此不疲。對這一切我們怎能不深表憂心呢?感恩祭是一項厚禮,不能讓它的意義變得模糊,並受到輕視。
我希望這篇通諭能有效地幫助我們,驅除那些我們所不能接受之教義和習慣的烏雲,使感恩聖祭能繼續散發這光輝奧蹟的所有光芒。」(10節)
除了侵害禮儀的做法之外,也有人對官方公佈的改革,反應敵視。這些人認為,改革過度及過急,也有人甚至認為官方的改革,有違反教義之嫌。還記得1969年出現的爭議:當時,奧提維 (Alfredo Cardinal Ottaviani) 和巴捷 (Antonio Cardinal Bacci) 兩位樞機,寫了一封信給保祿六世,表達他們一些非常嚴重的憂慮,而之後教宗亦判斷,為此作出一些教義上的澄清是合適的。這類問題,同樣,需要仔細分析。
可是,這裡也有一個牧民現實:無論有否適當的理由,有些人就是不參與、或者不願參與改革後的禮儀。這些人遠離禮儀,或者只參與他們找到的、未被改革的禮儀,即使這些禮儀是未經批准舉行的。這樣,禮儀竟成為教會分裂,而非大公教會團結的標誌。大公會議從未希望禮儀分化我們!聖若望保祿二世,下了苦功去醫治這個創傷;在拉辛格樞機,即日後的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協助之下,又嘗試推動教會內部必要的修和;後者的自動手諭《歷代教宗》 (Summorum Pontificum) (2007年7月7日) 訂明,更古老的羅馬禮,應毫無阻隔地,開放予那些希望從中獲取其豐富寶藏的個人或團體。在天主的眷顧下,我們現在可以在慶祝我們大公團結的同時,尊重甚至乎歡欣鼓舞於禮儀儀式的合法多元。
最後,我也想提到,大公會議後的改革和翻譯過程﹝我們知道部分工作太過倉促,以致今天我們要修訂這些翻譯,使它們更忠於拉丁原文﹞,可能留意不足會議教長們所說、所追求,以達致有效參與禮儀的要訣:即教士們「應徹底充滿禮儀的精神和權能,進而將之教導。」我們知道,一棟大廈建築在軟弱的根基上,具有破爛、甚至倒塌的風險。
我們可能利用白話,建構了一個嶄新、現代的禮儀,但如果我們沒有鋪設正確的根基—如果我們的修生和教士不如大公會議所想,「徹底充滿禮儀的精神和權能」—他們將不能培育那些被交付給他們牧養的子民。我們要非常認真地對待大公會議本身所用的字眼:追求禮儀更新,卻無視禮儀培育,將「徒勞無功」。缺乏這種必要培育的教士們,更能破壞人們對感恩(聖體/共融)奧蹟的信德。
我不想被視作無理的悲觀主義者;我在此重申:有許多、許多的男女平信徒、許多教士、修士修女,曾從會議後改革的禮儀,支取過屬神、傳信的果效;為此我是感謝全能天主的。不過,即使從我剛才簡短的分析來看,我相信你們也會同意,我們的確能夠比現在做得更好,誠如教長們懇切期望,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使神聖禮儀真實地成為教會生活和使命的泉源與高峰。
無論如何,這是教宗方濟各要求我們做的事:他說「有需要去團結一個更新的意願,邁進會議教長們所指出的道路,因為,為使信友及教會團體正確及完整地融會貫通《禮儀憲章》,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我所指的,尤其是需要一個穩固及有機的禮儀導論及培育的決心,這對平信徒及神職和獻身修道者同樣重要。」
【註】此中文譯本已徵得“Sacra Liturgia UK”批准及確認,並由《號角報》及《樂山樂水》網絡平台共同發佈。英文全文參見http://www.sacraliturgia.org/
 Follow
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