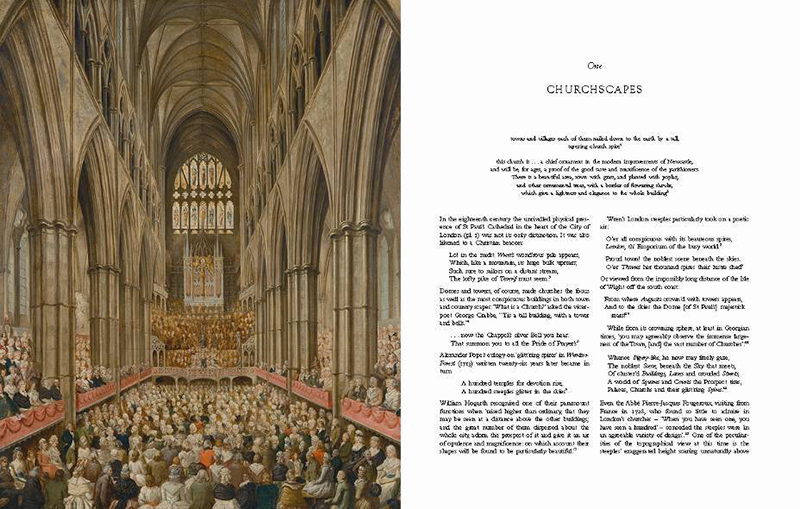【南京教難中的高一志(5)】南京教難對今天教會的反思
文:段春生神父
《辟邪集》關於高一志的肖像給我留下了珍貴的記憶:「王豐肅面紅白、眉白長、眼深、鼻尖、鬍鬚黃色。供稱年五十歲,大西洋人。幼讀夷書,繇文考、理考、道考、得中多耳篤,即中國進士也。不願為官,只願結會,與林斐理等講明天主教。約年三十歲時,奉會長格老的惡之命,同林斐理、陽瑪諾三人,用大海船在海中行走二年四個月,於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內,前到廣東廣州府香山懸香山澳中。約有五月,比陽瑪諾留住澳中,是豐肅同林斐理前至韶州府住幾日。又到江西南昌府住四月,於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內,前到南京西營街居住。先十年前,有利瑪竇、龐迪峨、郭居靜、羅儒望等,已分住南京等處。利瑪竇要進京貢獻,寄書澳中,到王豐肅處,索取方物進獻。是豐肅攜自鳴鐘、玻璃鏡等物前來。比時利瑪竇先進京,隨將方物等件,寄進京貢獻訖。比時羅儒望將家火交予王豐肅,遂在此建立天主堂,聚徒講教,約二百餘人。」
這份三百多字的訴訟記錄,非常形象地給我們留下了高一志的肖像描繪,也勾勒出了高一志在意大利接受教育程度及來到中國南京被任命為該地教會團體負責人的一個輪廓。
1617年3月6日,高一志被帶到沈㴶的禮部大堂,「王豐肅身著囚服,脖子上套着繩索,被牽了進來。」他被審訊了兩個多小時,「一直被迫跪着」。沈㴶宣布他們在中國宣揚的是一種新的宗教,本該處死,但由於皇帝仁愛,不忍賜死,要將他們遣送回國。然後,對高一志「杖刑十大板」。高神父後來回憶道:「過了一個月的時間,我的傷口才開始愈合……命我與他們一道,去對會院進行嚴密的搜查,將其中的書籍、手稿、聖像和數學測量儀挑了出來,沒收入官,送到了沈㴶那裡。會院中的家具沒有拿走,讓我處理。處理完了之後,我又被帶回監獄。」
1617年4月30日,高一志與曾德昭從牢房中被提出來,囚禁於裝死囚的木籠車中。高一志自述道,「我們的脖子上掛着重重的鐵鏈,手上帶着鐐銬,衣衫襤褸,頭鬆和鬍子已經幾個月沒有梳理了。」木車上掛着三個牌子,上面寫着:『犯人是邪惡之人,他們擾亂了社會的平安,傳播新的教義。禁止任何人與他們講話或者與他有任何接觸。』他們在木車上被關了四天才被放出來休息,南京的教友們一直陪伴着他們。後來有些學者和朝中「有職位的官員」來看望這二位傳教士,且以詩文相贈,「以示他們的情感,並且留下一些紀念品。來訪的朋友們對耶穌會士的不幸遭遇充滿了同情」。
1617年5月20日,經過一個月的長途跋涉,高一志一行終於抵達廣州,被關押在黑暗的牢房裡。高一志追憶監牢的環境,「又濕又小,流行着瘟疫,好多犯人擠在一起。在這裡是不可能躺下的,因為一伸腳就會搭在別人身上。」他們在廣州關押一個月後,釋放了出來,被安排住在一座塔樓裡。1618年,在高一志一行到達廣州七個月後,被知府轉交給澳門。
在漫長的教會歷史的長河中,教難從來都不缺少。天主允許這些教難發生,是要通過教難淨化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雖然教難時有發生,但教難並非基督徒追求的生活理想。
正如歷史是追求時間上的永恒,在歷史時空的延續中尋找生活的智慧。生活在現代社會的基督徒,也應從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的歷史經驗中汲取經驗和教訓,為的是獲得有益於當下教會發展的智慧。
事實證明,在明末清初時期的耶穌會士們,如果偏離了利瑪竇神父經過長期的實踐和反思所形成的「文化適應與學術傳教」的方法,就會付出流血的慘重代價。利瑪竇所開創的教會本地化的福傳策略,對今天教會的發展依然有其現實的意義。
全文完

 Follow
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