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臨終病人
文:Fausto Gomez OP
譯:何紹玲
為了在倫理上、神學上和精神上清楚地分析明顯在增長的安樂死和協助自殺等等問題,教廷信理部於2020年7月14日發表了一篇密集、頗長、有充分依據的文件,題為《慈善的撒瑪黎雅人》Samaritanus Bonus(SB),副標題為:有關照顧病危和臨終期的人。這文本共33頁,包括八頁共99項的註腳,已得到了教宗方濟各的批准。全文分為五個部份(I至V)。照顧身患絕症病人的守則,就是仿效那位「慈善的撒瑪黎雅人」,聖經中記載耶穌的一個家傳戶曉比喻:要懷着憐憫心和關切的態度(參閱路加10:30-37)。教會是老師,也是母親。
教廷信理部這份文件的宗旨是藉此啟發司鐸們和信眾(及所有護理人員)如何照料病危和臨終階段的病人,並指出他們是有義務陪伴病人跨越這些階段的。信函是希望能「重申教會的訓導。」信函在第五部分提出、解釋及闡釋這傳統的教會教導,更明確地排除了訓導文本因多次重覆至出現的含糊意思(SB,V,1)。
教會的訓誨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針對安樂死和協助自殺[的個案],也談及積極治療與緩和療護。安樂死的定義是「最終能導致死亡的一種行為或省略,借此方式去消除所有痛苦」。《SB》指出現在仍需要繼續「重申安樂死是危害人類生命的罪行,需明確正視」:都是違反自然律與神律主要的原則,在「任何情況和環境下,它的本質都是邪惡的。」安樂死是「惡意的自殺和謀殺」(SB,V,1)。
如果是實質性的去協助自殺(或直接幫助想要自殺的病人)是嚴重不道德的行為,(那些贊成安樂死的、或直接去幫助想自殺的病人)或直接在物質上合作(即那些口口聲聲說自己反對安樂死的人,卻提供想自殺的病人在物質上能致死的需要)。
此外,領導人、立法者、醫生和護士,以及建議和批准有利於安樂死和協助自殺等等不公正法律的人,也應為這邪惡和不合理的合作負責——他們是同謀!因為這是客觀上不道德的合作:它「侵犯了人的尊嚴、亦侵犯了生命罪和危害人類罪」(SB,V,1)。
每個人都應享有基本的生命權--但沒有死亡的權利:「 沒有自殺的權利,也沒有安樂死的權利;法律的存在不是讓我們製造死亡,而是為了保護生命和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共存。因此,去配合這種不道德的行為——不論在言語上、行動上或省略中暗示勾結——在道德上是絕不合法的(SB,V,9)。 在這種情況下,天主教機搆——也包括個別醫生或護士——都不應該幫助有意尋安樂死或協助自殺的病人轉介到其他醫院:這是不道德的合作(參照 SB,V 9)。
有真正良知的人會譴責不公正的法律,更會抗拒不道德的法律。如果有人要求合作實施安樂死和協助自殺,或以似乎道德的方式進行,他們應該施行憑良心拒絕的權利,堅拒合作。憑良心拒絕,是一種普世的人權,出於良心/宗教自由的表現。「各國政府必須承認在醫療和保健領域,仍有憑良心拒絕的權利。」因此,衛生保健工作者「應該毫不猶豫地要求這權利,好為共同利益作出貢獻」(SB,V,9)。
緩和療護
在生物醫學上,如一切也無助於臨終者,人的生命是可以人為地延緩的;然而,這並不是把生命延長,而是延長死亡。既然還有那麼多病人需要現有的稀缺資源,為甚麼還要使用無效的治療方法——積極治療——不惜一切代價去挽救生命?儘管大家都覺得積極治療是更人道、更基督宗教化和更公平——但它一般都被認為是可有可無的,只不過不想用對病人不利的治療方法而己。然而,是否使用特殊治療,便應該是危重病人的決定,可通過知情同意或替代式同意,利用預前指示或遺囑去表達。從病人入院的那一刻起,病人和醫生就進入所謂「治療契約」。
關愛病人永遠是醫療的目標;綜合醫療護理包括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治療和晚期患者的緩和療護(姑息治療)。當大家都認為安樂死和協助自殺是不道德地把生命縮短,積極治療和特殊治療是無效地延長死亡,姑息治療則全程陪伴着病人(和他們的家屬),讓他們在適當的時候離去,既不提前(如安樂死)、也不推遲(如無效的積極治療)。在醫學上、道德上和精神上,人們都應享有死的尊嚴——寧靜地、安詳地。
緩和療護是真正憐憫和同理團結最好典範的表達方式,它能處理三個重要的問題:疼痛、孤獨和被遺棄,以及絕症病人在精神上的需求。提供醫療保健的,主要是解決疼痛:盡量把它消除,至低限度也把痛楚減輕;家人和家中重要的成員可給予愛——讓他感到被愛——不可令病人陷入孤單或被遺棄的恐懼中;至於病人在精神上的需要,責任便落在牧靈團隊的司鐸、醫院的牧者及牧民組了。
緩和療護會提供對臨終者有幫助的治療,包括供給營養和補水療程,雖然這些本身都不算是醫療,但對臨終者和已處於植物狀態(PVS )的病人而言,是需要的。在「必須施用營養或補水療程時,可以用人工施予,只要做法不會對患者造成傷害或難以忍受的痛苦」(參照SB, V,3)。
與其他合作者,尤其是姑息性醫療,他們會企圖令病人覺得這痛苦是可容忍,甚至是有意義的。他們會開止痛藥,包括可導致病人喪失意識和縮短他們生命,稱為「深度姑息性鎮靜」的藥物(參照SB,V,7)。給病人配方止痛藥,目的是為了消除疼痛或減輕疼痛,但絕不是為了造成死亡,因這也屬於安樂死的一種做法(參照SB, V 11)。
說到做到
眾所周知,生命的基本和重要原則就是:從受孕到自然死亡那一刻,我們都必須捍衛每個人的生命。那麼,為何還有這麼多公教領導人、公教立法者、一些公教倫理學家、生物倫理學家和神學家,以及公教家庭都贊成墮胎、安樂死、協助自殺和死刑呢?生命教育是一種信仰的承諾……支持生命文化、反對死亡文化。在生命與死亡的問題上,任何相信耶穌是好撒瑪黎雅人、祂被釘死於十字架和復活的基督信徒,都不應袖手旁觀。「每一個基督信徒都必須感到這召喚,在苦難中為愛作見證」(SB總結)
在這差不多絕望的世界裏,我們還堅信希望的一群,都希望能找到期待永生的理由:「最大的悲哀在於面對死亡時缺乏希望(SB,V;總結)。我們希望並祈求耶穌能告訴我們每一個人:「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
「主啊!甚麼時候?」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參閱瑪25:31-46)。就讓我們懇求耶穌:「幫助我們成為慈善的撒瑪黎雅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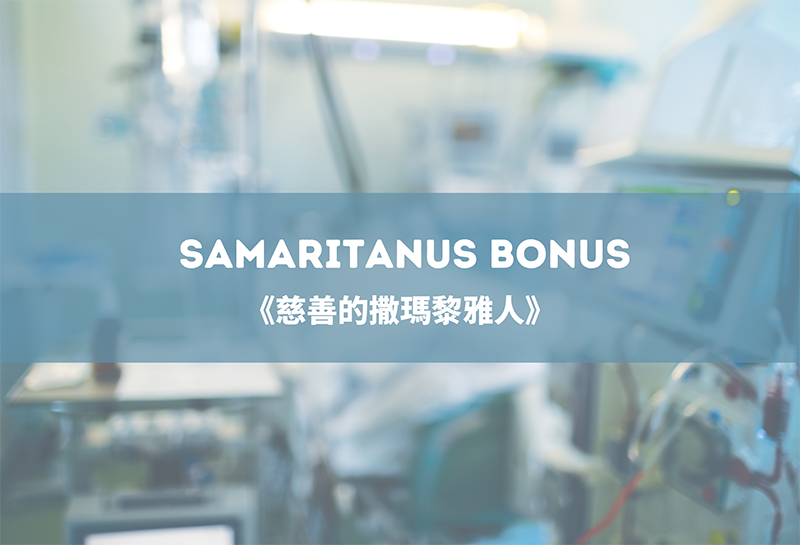
 Follow
Fol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