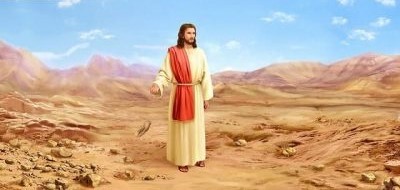文:饒安
基督信仰的種子,隨著英國第一艦隊(First Fleet)在1788年的抵達而開始在澳大利亞廣闊美麗的土地上播下,而本篤會在澳大利亞早期的開教和福傳事業方面曾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但促成聖統制在當地建立起來,本篤會士更出任當地首名主教的聖職。
天鵝河殖民地(Swan River Colony,即今天的西澳大利亞州,簡稱西澳)在1829年建立後,一些信奉天主教的英國殖民者出於信仰的需要而請求悉尼教區派遣聖職人員前赴當地。這自然少不了本篤會士的足跡,特別是其中的兩名會士塞拉(José Benito Serra)和薩爾瓦多(Rosendo Salvado)於1846年在西澳首府珀斯以北132公里建立的新諾爾恰(New Norcia)修院,更與西澳福傳事業的全程同行,饒具歷史價值和意義。筆者近月有幸造訪當地,願藉此文與各位分享所見所聞。

新諾爾恰除了有修院培育聖職人員之外,還肩負起向當地原住民傳播福音,向他們授予當代西方生產技能的使命。在西澳的本篤會士尤其對原住民的文化格外尊重,在當時而言還算是罕見的。進入20世紀,新諾爾恰的規模逐漸擴大,建立起兩所學校、一所修女會、一所修士會和一座旅館,大抵形成了今天可見的規模。正由於新諾爾恰在推動西澳偏遠地區的福傳和社會事業發揮重要的作用,當地曾經是澳大利亞唯一的自治會院區(territorial abbacy),擁有與教區相若的管轄權。隨著梵二之後自治會院區的建制逐漸被撤銷,新諾爾恰也不例外,於1982年改為堂區,歸珀斯總教區管轄。

在某些環境下,活生生的見證比起傳統的要理講授顯得更具說服力,也說明人受感召而皈依,總有上主自己的安排。新諾爾恰創業之初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在一切甚為艱難之時,不同文化之間的調適自然引起當地一些原住民對本篤會士的誤會,甚至懷疑。夏季的澳大利亞,尤其是內陸地區,氣候炎熱乾燥,極易引發火災。1847年12月,有一位原住民出於報復心理,向新諾爾恰的耕地縱火。由於正值盛夏,加上風勢強勁,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延綿長達一英里。就在千鈞一髮之際,本篤會士從聖堂的祭壇搬出善導之母畫像,到火場前熱切祈禱,懇求聖母助佑。果然,風向迅即逆轉,山火自行撲滅,墾殖的心血總算避過被火完全吞噬的厄運。這樣一來,既使早已追隨他們的原住民的信德越發堅定,更軟化了縱火者的心,從此成為修院的忠實夥伴,福傳事業的拓展也變得更為順遂。

本篤會士除了為西澳帶來基督的福音外,更為新諾爾恰留下大量珍貴的藝術遺產。這與曾於20世紀初出任修院院牧的托雷斯(Fulgentius Torres)在拓展新諾爾恰城鎮期間,注重建築物的藝術設計和裝飾不無關係。為了使建築物的藝術品盡可能達至最完美的境界,托雷斯特別從西班牙商請擅長木雕和壁畫的藝術家,為當地聖堂、學校和修院建築創作一系列的精品,部分現已成為博物館或藝術館的藏品。

雖然目前新諾爾恰的規模和影響力,隨著澳大利亞社會世俗化的深入而有所褪色,但當地至今仍然是澳大利亞唯一的修院城鎮,為本篤會繼續培育所需的聖職人員。就在以原住民為收生對象的兩所學校,以及新諾爾恰天主教書院相繼停辦的同時,新諾爾恰修院積極利用本身累積經年的各類文獻,建立起具一定規模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並為西澳偏遠地區的牧民培育工作、歷史文化研究以及信友的靈修提供場所和便利。修院方面也非常重視對文化遺產的保育,除了修復、活化和再利用城鎮內的建築物和聖堂外,近年為修院歷來使用過的近1200件祭衣建立新的儲存設施,又成功爭取到澳大利亞國家信託基金(該國的文物信託機構)為文物修復的捐獻提供免稅安排。加上修院本身一直經營的麵包、橄欖油、啤酒製作和旅館業務,新諾爾恰正以另一種方式,傳承百多年前本篤會先驅所開創的福傳事業。

 Follow
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