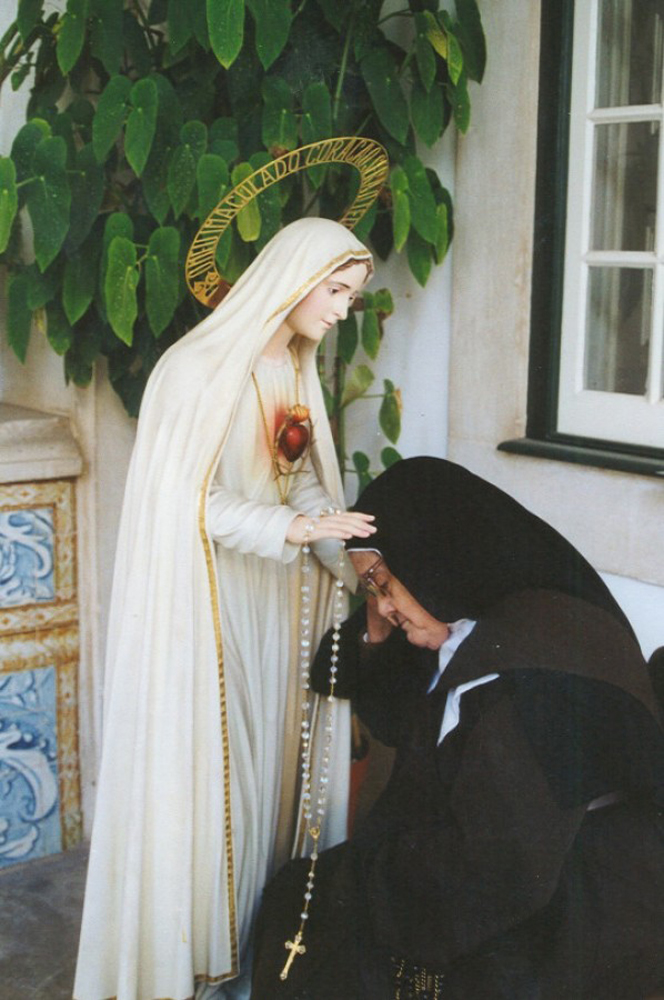文:Michał Kłosowskki
在教宗方濟各登上前往巴格達的飛機前,這朝聖訪問伊拉克之行不可能是真實的,正如很多人認為這並非明智之行。為我們記者而言,前往伊拉克更是一個挑戰;無止境的戰火、疫症的蔓延,絕非好的時候。然而,聖父十分堅決的要訪問伊拉克(3月5至8日),也就是教宗新冠疫情後的首個牧靈之旅。當然,在嚴格的保安措施下,教宗的行程一如既往地緊湊:教宗將穿梭整個國家。若不是教宗的到訪,誰會願意忍受被數百萬人——大部份基督徒——的騷擾?不少人認為,教宗訪問伊拉克是帶來麻煩的,但為更多的人——不止在中東地區的人——卻認為教宗之行是「希望」的訪問。
與上一次的牧靈訪問(泰國和日本)已有一年之多,在此期間,教宗不停地呼籲,要這充斥着混亂與衝突的世界中,尋求和平。我與參與牧靈訪問的人交談,聆聽他們的分享:我們談論到信仰的基礎,也就是廿一世紀中定義基督宗教最重要的思想。
現在,教宗將到訪一個人民經歷着及遭受着無數痛苦的地方,這些痛苦同樣是廿一世紀中發生,而且都是難以想像的。
在一個充滿血腥——經過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統治、遭受內戰與經濟困擾——的土地上,教宗的到訪意味着呼籲:一、和平;二、兄弟之情;三、放棄一切武力的解決方案;和四、共同(作為人類及共同信仰的兄弟姊妹)來面對未來的挑戰。
但對於許多伊拉克人來說,基督宗教十分陌生;那裡沒有像在法國般的大教堂,沒有像在德國般的天主教團體。教宗方濟各再次到訪伊拉克的外圍、邊境地區,只有在流血事件發生時,這些地方才被關注。然而,這地區——從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發拉的河(Euphrates)肥沃之地——是一神論宗教的搖籃;此外,伊拉克南部的烏爾(Ur)古城更是信德之父亞巴郎的出生地。基督徒在公元第一世紀到達那裡時,也目睹聖神降臨。然而,在數百年後的七世紀、阿拉伯人徵用了這些土地後,基督徒雖然不用被迫改變信仰,卻要上繳宗教稅;他們建造城市,創立社區團體。在1990年,伊拉克仍然有120萬名基督徒,到了2003年更增至150萬名基督徒。但在2003年至2014年間,伊拉克國內的基督徒減至135萬人,全因宗教迫害的緣故。在2009年,摩蘇爾發生了一系列的炸彈襲擊,逾過半的基督徒自此逃離這座城市;甚或更早,在2006年,摩蘇爾的瑪.保祿.法賴吉.拉霍(Paulos Faraj Rahho)總主教被謀殺,據稱他被斬首,屍首更慘被砍碎並丟進垃圾桶裡。
伊拉克的基督徒,被視為西方國家的合作者。在一個伊斯蘭與基督宗教鬥爭的氛圍下,穆斯林驅逐基督徒,並私下進行迫害基督徒的行為,如殺害基督徒、綁架婦女和兒童、破壞聖堂等等;就像數年前曾不時見過的⋯⋯
教宗方濟各對外公布訪問伊拉克,令世界各國都期待着。伊拉克現任政府形容,教宗計劃的朝聖之旅,是歷史上的一項創舉,也是為該國與整個地區帶來和平的象徵。但是,伊拉克國內的情況仍沒有穩定;教宗的牧靈訪問,可能就是改變的唯一希望。
前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曾計劃到中東這些地區,包括伊拉克、埃及和以色列,進行牧靈訪問。不過,前伊拉克統者者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沒有允許;其後便迎來一系列的戰爭及美國的干預。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預言美國的干預是「一場噩夢和不可逆轉的現實」。後來,又出現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再來的是長達數月的流血衝突、示威和暴動,參與的都是年輕的伊拉克青年,他們要求進行改革並堅決打擊腐敗;然後,便是現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
新政府於去年5月成立,有宏偉的計劃;國內各界亦為將於今年6月舉行的國會選舉作準備。教宗到訪的原意,就是要鼓勵該地區的改革派支持者與和平派的分子。
為一個現時需要專注於應對疫情的全世界來說,教宗今次的牧靈訪問可能是一個問題;為那些希望衝突及激進主義者來說,也是一個問題;因為教宗的訪問打着和平的旗號,要求控制、消除激進主義及建立理解橋樑的訊息。底格里斯河上尚存的兩個摩蘇爾橋樑,可能就是今次訪問的象徵。
行程中特別重要的,就是教宗方濟各將與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領袖希斯塔尼(Ali al-Sistani)會晤,而會面地點將在厄則克耳先知的墓穴附近舉行。曾在2001年至2006年間擔任駐伊拉克和約旦代辦的斐洛尼(Fernando Filoni)樞機曾形容,厄則克耳安慰了囚禁在巴比倫的以色列人:「並給予他們希望,天主會將生命注入已逝的骨灰上。當我在厄則克耳的墓穴祈禱時,我曾看到有穆斯林信徒也到此處。教宗的到訪帶來希望,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關係,也將得到生命的希望。」
而今次牧靈訪問伊拉克的主題就是:希望。
作者為波蘭報章《一切皆重要》(Wszystko Co Najważniejsze)副總編輯

 Follow
Follow